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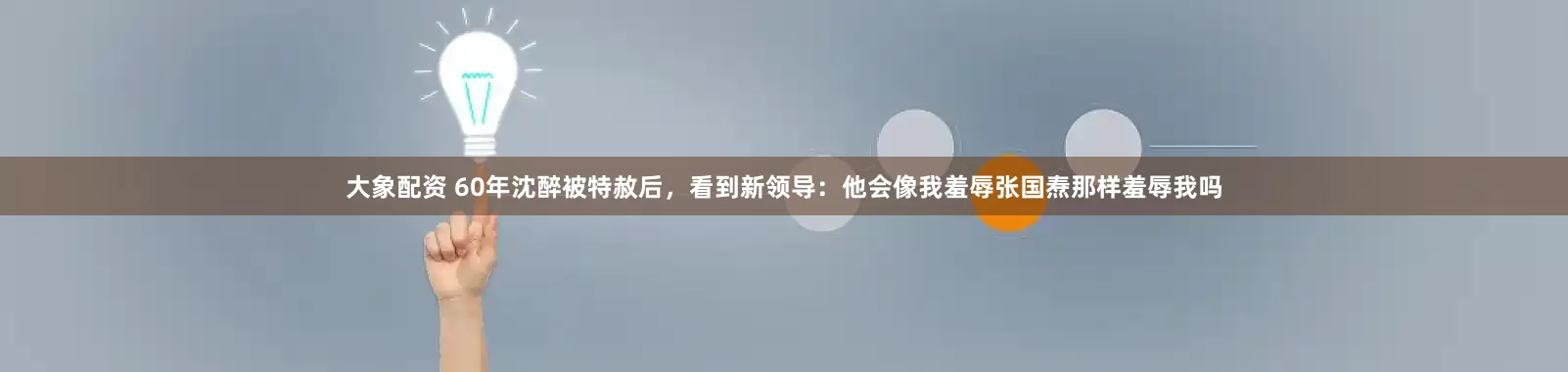
“老廖大象配资,我是不是快自由了?”1960年12月14日清晨,沈醉压低嗓子问站在铁门旁的管理员。对方只是笑笑:“先去食堂搬桌子,别多想。”一句模棱两可的话,让沈醉心里七上八下。
半个月前,他在《人民日报》角落里发现“国务院第一○五次常务会议审议第二批特赦名单”一行小字,那天夜里他用被子裹住头,翻来覆去睡不着。自己到底会不会在名单里?想想当年在军统里杀伐果决的样子,如今这种惴惴不安,让他觉得脸上发烫。

搬桌子时意外发生了。他端着一盆月季,脚下打滑,啪的一声,花盆碎成几瓣。空气仿佛凝固。他赶紧举手认错,以为又要写检查。管理员摆摆手:“没事,赶紧收拾。”那语气像对待普通同事,而不是昔日军统少将。沈醉心里一动,却也不敢多想。
午后,布置好的礼堂坐得满满当当。宣读开始,名单一个接一个。沈醉先前的雀跃慢慢变成木然,他甚至出神地数着屋顶的灯泡。突然,法官念到“沈醉”。他没反应过来,旁边的管理员推了他一下,他才冲上讲台。手里的特赦证书微微颤抖,眼前一阵潮湿,字都看不清。
特赦的法律依据其实不复杂——1959年《宪法》修正后,国家主席有权对战争罪犯实施特赦。第一批千余人已先行释放,第二批中为什么会有自己?沈醉后来回忆大象配资,那一刻除了感激还有疑惑:我真配吗?
放出来不到四十八小时,组织通知他去北京工作,接受市委统战部领导。领导人选三个字——廖沫沙。沈醉心里“咯噔”一下:这不是当年军统黑名单里排前十的“赤匪”吗?更要命的是,他还记得自己当初怎么奚落张国焘,如果廖也拿这套回敬自己,那可真是报应。

火车从南京一路北上,窗外枯草连天。他闭着眼,往事却闯了进来。1941年,军统一次购入四辆崭新的别克。张国焘派人来要车。沈醉一句“给他派三轮”,把原延安中央委员硬生生驱赶到雨中。张国焘淋得像落汤鸡,冲进车库破口大骂。沈醉冷笑:“这里可不是延安。”张国焘气得眼眶通红,却只能干瞪眼。台阶上那声回荡的“不是延安”,像钉子一样钉在沈醉记忆里。
北京的冬天刮着刀子似的寒风,统战部办公楼却暖气十足。见面那天,廖沫沙摘下帽子,第一句话竟是:“沈先生,路上辛苦了。”沈醉愣了,急忙低头:“过去多有冒犯,请您恕罪。”廖沫沙拍他肩:“别背包袱,我没记仇。”短短一句,像拨开厚冰的暖流。
可沈醉还是不踏实。1961年春,他想去广州接前妻。按惯例,离京须批条。鼓起勇气去找廖沫沙,本以为要层层汇报大象配资,没想到廖当场签字,还脱口一句:“路费够不够?不够跟我说。”沈醉哽住,只能连声说好。

出发前一晚,廖沫沙邀他小聚。老式胡同,小木桌,几碟花生米,一壶二锅头,没有任何说教。廖举杯:“特赦不是句号,是逗号,你日子还长。”沈醉手心冒汗,还是把酒一饮而尽。那一声脆响的碰杯,让他忽然明白,自己再不是待审的战犯,而是被国家重新接纳的公民。
为什么会这样?沈醉后来总结,一是法律框架先行;二是政策思路——“区别对待,既往不咎”。党内对此有共识:以民族大义为重,别让私人恩怨绊住脚。放下屠刀、洗心革面,这句话不是空洞口号,而是对稳定局面的现实需要。不得不说,这种胸襟,让曾在军统摸爬滚打的沈醉都心生敬佩。
不久之后,沈醉被安排在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搞口述史,起初他担心没人理睬,一个电话打去,居然有老党员主动来对接。有人提醒:“你了解国民党高层内幕,这是财富。”沈醉这才意识到,原来自己也能为新中国出点力。
再往后,沈醉把在戴笠手下十多年的档案、代码、暗号与处置经过,一点点口述下来。每一次录音结束,他都会长长吐气,“这算赎罪,也算交代。”整理材料的年轻女党员笑说:“先生,我们不是要你赎罪,是让历史说话。”那一刻,他才真正放下心头大石。

多年以后,有记者问他:当初最怕什么?沈醉答:“怕报复,怕羞辱,更怕没人相信我能改。”停顿片刻,他补了一句:“其实是自己没放过自己。”旁人无言。
张国焘的三轮车往事,仍被旧友当茶余饭后趣谈。有人调侃他现世报。沈醉笑笑:“真报的话,也许没有今天这杯热茶。”说罢,他端起杯子,轻轻吹了口气,茶香袅袅升起,飘散在安静的屋里。
恒正网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