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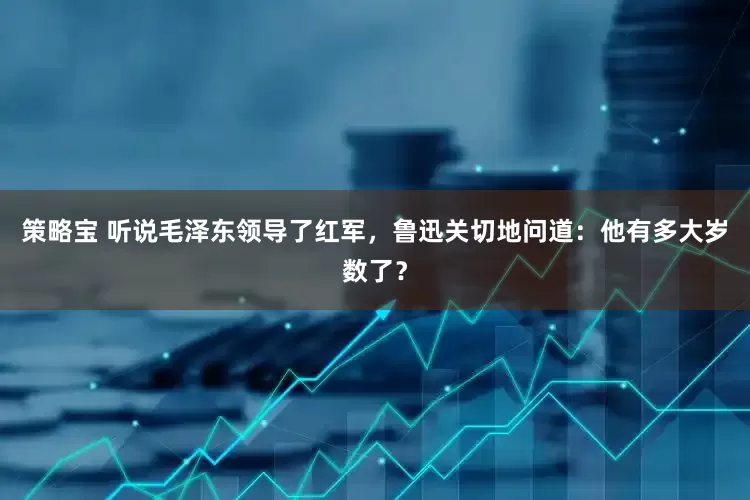
听着,1931年9月的午后——“朱毛把老蒋吓坏啦!”鲁迅晃着报纸嚷了一句,茅盾端起茶碗答声“可不是”,话音刚落,鲁迅眯起眼又追问,“那位叫毛泽东的策略宝,他今年多大?”
毛泽东那时三十八岁,远在江西指挥红军,却不知道京沪文坛里有人这样惦记他。实际上,两人第一次出现在同一座城市要追溯到1918年的北京。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搬书、抄卡片,月薪八元;鲁迅则常去三院课堂,也爱买古旧线装书。可惜一个忙着筹印《新青年》增刊,一个埋头给学生改作业,时间错得刚刚好,擦肩而过。
李大钊看人很准,他对毛泽东说:“你多和胡适、周作人聊聊,眼界会开得更快。”毛泽东照做了,也专门跑到周作人家里问白话文创作的门道。周作人笑谈时提到“我大哥写了篇《狂人日记》”,毛泽东当场把刊物翻完,只留下短短一句:“笔锋够辣。”谁都没料到,这位馆员后来会把笔换成枪。

1927年南昌枪响、秋收起义,毛泽东转身上了井冈山。上海的《申报》天天骂“朱毛匪部”,越骂名气越大。鲁迅最爱看广告栏下面那几条社会新闻,他看见“毛匪”二字,抬手点了支烟,对冯雪峰说:“北洋时期看他是书生,如今倒像真会打仗了。”冯雪峰笑:“书生也能带兵,先生信不?”鲁迅没接茬,却在日记里加了一行:“须多留心湖南人。”
第三次反围剿被红军粉碎后,国统区忽然弥漫“朱毛要北上”的传闻。那天鲁迅、茅盾、冯雪峰三人凑在一起校稿策略宝,谈到这里,鲁迅把眼镜往上一推:“蒋介石怕的不是兵,是‘农民起来’这四个字。”茅盾回忆自己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见过毛泽东,“人不高,嗓门大,讲话像打点子鼓,很会把复杂道理掰碎了说。”鲁迅听完点头,轻声一句:“难怪。”
1936年春,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带回“红军长征到陕北”的第一手消息,鲁迅病榻上立刻提笔写贺电。那份热烈的文字后半夜才完稿,他吩咐:“交给雪峰,让毛泽东知道,还有人记得他们。”电报经武汉、延安几经转手终于送达,毛泽东看完连说三遍“先生胸怀天下”,随后拍板:派冯雪峰进沪,建立秘密电台,也带一句口信——“山高路远,心同此心”。

冯雪峰回沪见鲁迅时,门外是特务的黑影,屋里却点着昏黄油灯。鲁迅听完口信,很痛快:“电台我来负责,缺电池就找内山完造。”说到毛泽东,他忽然笑出声,“将来若见面,我只问他读没读过《风声雨声读书声》。”冯雪峰在回忆录里写:“那笑容像久旱后的雨。”
鲁迅终究没能等到会面。10月19日凌晨五点,病情恶化,他叮嘱许广平:“雪峰若到,告诉他,红军要严防内奸。”话音落下不久,心跳停止。三天后,延安的短波里传来噩耗,毛泽东沉默很久,只拿毛笔写了四行:要求国葬、致许夫人唁电、告同志书、令雪峰主持丧事。字字直戳人心。
延安随后建起鲁迅师范、鲁迅艺术学院、鲁迅图书馆。开馆那天,警卫递给毛泽东剪彩用的丝带,他挥手:“不用此俗。”转身走进阅览室,随手抽出《故事新编》,扉页空白处写下:硬骨头策略宝,热心肠。
1940年夏,萧军进延安。毛泽东见面第一句话不是问创作,而是:“先生笔下的‘子君’,有鲁迅影子不?”萧军愣了下才答:“恐怕还是像您多些。”两人哈哈大笑。后来延安文艺座谈会定稿,毛泽东在稿纸边角浓墨写下四字:学鲁迅法。

抗战胜利、解放战争、建国,“鲁迅”这个名字始终跟着毛泽东的批注本一起上火车、进窑洞、登飞机。1956年《鲁迅全集》出版,毛泽东一次性买了三套:一套放中南海,一套送湖南老家,一套随身。张玉凤回忆,主席常拿铅笔圈出段落,旁边写“此语中肯”或“改天议”。
1961年鲁迅八十诞辰,毛泽东夜里写下两首七绝,挥笔极快,墨迹却稳。警卫看不懂“鉴湖越台名士乡”一句,他抬头解释:“绍兴出刀笔吏,也出真豪杰。”说罢把稿纸合上,“给新华社,别改韵脚。”
年老视力衰退后,他仍记得鲁迅诗里的那句“花开花落两由之”,和唐由之医生肖同字更显巧合。唐医生感叹:“主席记忆惊人。”毛泽东摆手:“我只背熟了一个人。”话没说透,但谁都明白,他指的是鲁迅。

1976年9月,毛泽东在游泳池边的小屋里度过最后一个夜晚。案头除经典兵书外,还摊着大字号《吶喊》。护士要收拾,他摇头慢慢合上书:“留着,明天再看。”那天之后,再无人翻动那本旧书,可书页间折痕尚新,似乎刚刚被人指点过最锋利的句子。
两位并肩而未谋面的巨人,一个用笔解剖旧社会,一个用枪劈开新世界;不必同桌饮酒,彼此却早已在对方的时代里留下深刻脚印。嚼起他们的字句与行动,会发现一种顽强的共振——对麻木说不,对黑暗开火。
恒正网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